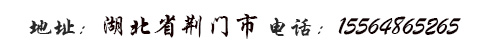宁建成丨柿子红了
|
我终于踏上了故土,妥妥地放下心来。正好秋风送爽,雁阵横过了长天。地里的豆子黄了,谷子黄了,树上的柿子也黄了……距离霜降还有些时日,显然不是层林尽染的好时候,但手搭凉棚四下张望,一树苍翠已遮不住炫目的亮黄了。 怎能不激动呢? 已十五年了,我奔走于他乡,故园的秋色只能在想象里铺开。今天看过来,庄稼长在低处,柿子结在高处。这些波澜壮阔的黄,像不像流落民间的君王,朴素的青衫掖不住的一袭黄袍? 如何不念想呢? 记忆深处太多的细碎,像不像一枚枚烘柿,有着甜蜜的浆汁?也有没烘透的,拌一口涩涩的“面疙瘩”,伸脖子瞪眼儿,也就咽下去了。 竟然不知从何处说起了…… 每年春节过罢,我要出门讨生活了。父亲把我送到村口,大柿树下作别,村路蜿蜒向远,如一根细长的缰绳,把我牵走了,也扯疼了父亲苍老的心。一别就是一年啊!大柿树一定记下了,每次相送之后,父亲的守望与迎迓。多少个黄昏里,父亲站在村口,站成老柿树的模样,凝望着长路与远山,随后被夕光慢慢地剪影了。 而我只能怀揣乡愁,在他乡的楼顶上,遥望着西北偏北的故乡——仿佛看见炊烟袅袅升起,高过了村口的大柿树,一对归巢的喜鹊喳喳地叫了两声,暮色愈发苍茫了。那一支熟悉不过的童谣,犹在耳边来回地唱——“花喜鹊,尾巴长,娶了媳妇忘了娘……” 大柿树是洪涛哥家的,更是乡亲们心中的“神木”。它像先人一样看护着家园,不知道有多少个年头了,两个成人才能合抱起来。触目惊心的是,一道深深的裂缝贯穿了树干,像没有愈合过的伤口。树心早已朽成了树洞,但它凭借庞大的根系和最后的年轮,替整个村庄活着。小时候月光下藏猫猫,树洞里一钻,不知不觉就睡着了——它为我们遮挡过多少夏夜的露水和秋夜的风霜呢?听老年人说过,大柿树要成精,遭到了雷劈,但我们从来没有害怕过什么的藤精树怪。 前年回家过春节,看到大柿树已钉上了“古树名木”的标识牌,说它已有岁的高龄了。随手拍了几张图片,发了朋友圈,问“谁认识它,谁知道它是谁家的柿树呢?”没想到竟有二十几位宗亲先后相认了——远嫁的姑姑看到它,像是回了趟娘家;儿时的玩伴看到了,像是找回了少年;外地讨生活的兄弟看到了,像是遇见了亲人…… 其实,每一位离人都有一方故土。譬如一条清溪,一个池塘,一棵大树……你若动了归心,它们就是故乡。 大柿树算是村子里的“老寿星”吧。还有更多的大柿树,矗立在流水一样时光里,托举着我们的童年。它们是如此地守时,四月里萌芽,绿荫热闹地铺开了;五月里开花,安安静静地凋零了。我们就小心翼翼地捡起来,穿成长串儿,焐上三五天,柿花便褪去苦涩,有了丝丝的甜意。挂在脏兮兮的脖颈上,菩提子一般的,我们就有了小沙弥的模样,双手合十,念“阿弥陀佛”,招来大人们的白眼与斥骂。骂就骂吧,反正我们不懂得眉眼高低。“佛珠”吃完后,小和尚做到了尽头,盛夏来临了,知了攀上了高枝儿,像一只只铁哨子,不知疲倦地吹。而青柿子藏在虬枝绿叶里,不紧不慢地生长着……可急死人啦! 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深秋,霜润柿尤红。放学了,抓块凉馍,有根大葱最好,没有也不会计较,然后挎着小竹篮,南岭北坡摘烘柿去。小时候我们身手敏捷,像小猴子一样麻利,连夹竿也懒得扛了。只要爬上了柿树,我们先把小肚皮招呼得滚瓜溜圆,虽然大人们不止一次地告诫,刚摘下来烘柿,性暴,不宜多吃,但小馋猫们就是抗拒不了彤红的诱惑。偶尔吃坏肚子,胀得像小皮鼓,敲起来咚咚地响,但稍自在一点儿,又照吃不误了。 那个时候,我们热衷于比赛爬树。好像最红最甜的果实,总是长在最高的枝头上,谁若摘下来,就有一种众星捧月的感觉,多么了不起似的。只是有一天,有个叫凤彩的妹子踩断树枝,折了腿骨,我们才收敛了几天。后医院接好了,听说治疗期间,遇到了西石村的黄医生,给予了力所能及的照顾。本家叔叔一直感恩有加。 就这样,我们不知不觉地长大,像斑驳的树皮下隐匿的年轮,藏不住高挂在枝头上的第一枚柿子……哦,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,我一直以为柿树是柿核长出来的,一次次地埋入泥土,等待发芽。直到有一天,父亲告诉我,柿树是软枣嫁接的,我才注意到每棵柿树的腰围上,都有一圈伤痕,腰斩一般地分开了它的今生与前世。这才明白柿子五花八门的品种,原来是主人左右的。譬如老家的柿子,品质上乘的就有六七种,如牛心柿子,大门定,摘家烘,马奶头……它们个大皮薄,汁水丰腴,算是柿子中贵族。平民化的有早熟的“八月黄”,晚熟“鸡心”……还有“小红柿儿”和“铁蛋儿”,一个像羞涩的乡下丫头,被秋霜洇红了脸蛋儿;一个像不安分的乡野少年,在南岭北坡的地堰上撒欢儿。但它们品质是有区别的——“小红柿儿”果肉甘甜,很是招人喜欢,而“铁蛋儿”皮厚核多,没什么吃头,乡下人常拿它做柿子醋。 我们家共有四棵“鸡心”和一棵“摘家烘”。听说是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,“前人栽树,后人摘果”,这是对萌庇最好的解释吧。那棵“摘家烘”已过于老迈,枝桠已腐朽了大半,像老年人患上了的骨质疏松,难以擎起一个成人的重量。但每年仍兢兢业业地开花结果,能够摘下来的却只有一少半。剩下的一大半,挂在高高的枝头上,款待着南来北往的鸟雀——“喳喳”叫的喜鹊飞去了,“嘎嘎”叫的灰鹊飞来了……这是慷慨的秋天,馈赠给它们的盛宴。而我们只能站在树下,仰着细长的脖子,等待掉下一个“老鸹叼”来……后来“摘家烘”寿终正寝,解成了厚厚的板材,父亲合了两幅案板,再后来分家时,我们和哥嫂家各分了一副。每当在案板上“笃笃”地切菜,就不由自主地想到连根共树的另一副案板来…… 唉!小时候不懂砧木的伟大。若干年后妻剖宫产生养了小女儿,腹部留下了一道横切的刀疤。一瞬间就顿悟了:重生,源于母体的伤口和疼痛。也想到了自己的“十年树木”,上五年级的时候,在自然课本里学到了嫁接。恰好西南坡自家的地堰上,有一棵不大不小的软枣树,很合适的砧木。也许是兴趣使然,找来了牛心柿子的接穗,手忙脚乱地一通捣鼓,用劈接的方法,泥巴封了刀口,塑料薄膜缠了又缠,最后草绳固定,细致得像是主任医师做了一台大手术。后来,接穗在砧木剖宫产一样的刀口上成活了,第五个年头上,居然结了三个大柿子,难免沾沾自喜,以为这棵柿树就是我留在人间的永久的纪念品了。但年冬天,不知哪个放羊的烤火,燎着了柿树底下的一堆秸秆,把正处于盛果期柿树烧成了黑炭。我得知后,心痛不已,爆了粗口骂了娘。 老家的柿子,寻常得如萝卜白菜,算不上精致的水果。乡下规矩挺多,院子里不种韭菜,也不栽柿树,大概与“割头”和“死”有关,讨不到好口彩。所以柿树大多散落在了村子周围,根本不需要管理,时令一到,就交出一树红彤彤的好果子,任由人们坐享其成。 其实,柿子食用方法还是挺多的,最简单就是吃烘柿。譬如摘家烘,皮薄少核,烘得又快,“摘到家里就烘了”,是烘柿中的上品,摊在墙旮旯,轰轰烈烈地烘开了,吃不及的时候,就烙柿子饼。发好玉米面粉,烘柿去皮,搅乎均匀,揉到软硬适中,铁鏊子麦秸火,焙得两面棕黄,吃起来又香又甜。不敢多说,又流口水了。还有晚熟的“鸡心”,极耐存放,房坡上铺谷草,倒上柿子,再盖好秸秆,防止鸟雀偷嘴,能存放到来年打春。尤其大冬天里,冻得像铁球一样的柿子在炉火边一点点地融化,煨热,吸溜一口,甜甜蜜蜜的浆汁不带丝毫的暴戾。另外漤柿也是极好吃的,需要水分较大的牛心柿子,温水浸泡去涩,漤到脆甜爽口。漤柿子对水温的要求极高,不能过热,不然就煮成了黑蛋子,析不出涩味来。水过凉了,还需要换水,前后需要五六天的时间,吃个漤柿也挺不容易的。但有一种方法,我们屡试不爽,就是在小河边上掏出一个深洞来,放入十几只青柿子,河水哗哗地流淌,涩味自然带去了,但需要七八天的时间。我们都是急猴子,第三天就开始品尝了,到头来也尝不到什么甜头。 最爱吃的莫过于柿饼了。每年深秋,地里农活忙罢了,摘来晚熟的“鸡心”柿子,父亲砍来榆树梢儿,祖母和母亲就开始旋柿饼了。看上去和削苹果皮一样的简单,但要旋得厚薄均匀,也是不容易的。柿子旋好后,缠在柔韧的榆梢上,吊在屋檐下晾晒,垂下一嘟噜的金黄。晾晒罢了,入坛子密封,一等一的美味就交给缓慢的时间了。等到年底开坛,柿饼就挂上了一层白霜,果脯晶莹剔透,软糯适中,就是甜得不讲道理……旋下来了柿子皮,也舍不得扔掉,簸箩里晒干,铁锅里焙焦,石磨上推成细面,抓上两把入碗,加少于白开水,搅拌成糊糊,像加了蜜糖的面酱,特甜。馋得我们伸长了舌头,小狗娃一样地舔,干净得都不用刷碗了。 这一切,仿佛遥远了…… 这些年来流离沪上。宿舍楼旁边的隙地上,恰好有两棵果木,一棵是柿树,另一棵不是柿树。是橘。都说南橘北枳,老家是不产橘的,所以稀罕了。只是橘子青黄的时候,偷来品尝,差点没酸掉大牙,也就不待见了。但那棵矮冠的柿树,该开花的时候开花了,该结果的时候结果了,该成熟的时候就熟透了。似乎是邻家的小妹,嫁到了江南,于是我便像娘家人一样关心了。 今年,也许是柿子的大年吧,稠得压低了枝头。眼看着秋深柿红了,我踅摸了十几只,晒了朋友圈,说自己近二十年没吃过漤柿了。洛阳姓水的文友留言,“这个,可以有。”说是柿子蘸过白酒,保鲜袋密封,一星期后就是漤柿了。我如法炮制,只是第五天头上,又像小时候一样猴急了,拆封品尝时,已没有丝毫的涩味了,琥珀色的果肉又脆又甜,果断地发了朋友圈,说什么“美味在于嘚瑟”。好友纷纷点赞和留言——“除了甜味,还有贼味”、“据说有高浓度的致癌物质,我们替你受难吧”……也有人询问是如何漤制的,就如实地告知了。正是洛阳好友的关怀,我乏味的生活才有了笑点和亮色——算是“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”的交情吧! 我终于写完这些文字,已经更深人静了。借一杯温吞的绍酒入梦,可有一棵老柿树,像我仙风道骨的先人,我们排资论辈,说到砧木,说到故乡,说到一树玲珑的灯盏,照亮了归心…… 作者简介 宁建成,“灵秀杯”征文大赛特等奖获得者。网名钓叟——非鱼而渔,一匹被生活与远方牵走的老马。家乡与诗歌,是他锲而不舍的真金与白银。首届“灵秀杯”原创文学大奖赛特等奖得主。 朗读者简介 王亚鹏,洛阳偃师人,从小热爱诵读,现洛阳朗诵艺术学会会员,偃师红树林艺术教育~~培林语言公益诵读课老师。 大赛详情,请打开链接: 第二届“灵秀杯”原创文学大赛征稿启事 “灵秀杯”参赛作品豆腐坊(宁建成) 灵秀之家赞赏 人赞赏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hongtiankui.com/htkxzjb/4086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皮肤干燥细纹红血丝跟这些问题说
- 下一篇文章: 刷爆小红书的网红美食清单新品,成都